2015-12-30 【凤凰网江苏频道】
在刚刚结束的“南京传世名著”评选活动中,作为南京文化大家的陶思炎推荐了一部将南京展现给世界的作品——《金陵岁时记》。他言,这是第一部记录南京地区岁时民俗的著作,它成书于民国,凡88条目,从元旦到除夕尽录南京的特色民俗和历史趣闻,涉及年节礼俗、交际游艺、庙会信仰、民间艺术、特色食品等方面,成为展示南京乡土文化的特殊窗口和研究南京民俗的珍贵文献。
术业有专攻。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民俗文化学博士,虽已迈入花甲之年,但仍旧笔耕不辍的研究家乡南京的民俗文化。在第三届南京文化名人揭晓之际,凤凰江苏第一时间约请陶思炎先生,首先祝贺他的当选,然后与他聊起了记忆中的南京。
这一天,恰逢冬至节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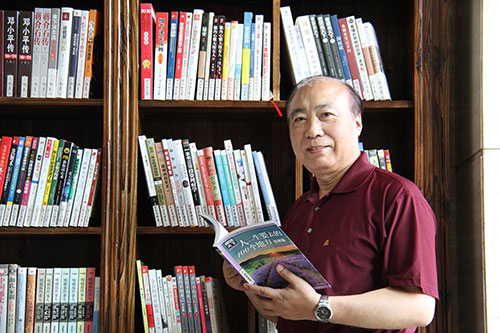
陶思炎
追忆80年代:文学在校园里复活
1977年,受“文革”冲击而中断十年的高考得以恢复。第二年夏,陶思炎参加了第二届高考。
“相比较77年高考的一系列的限制条件,78年高考对老三届没有年龄上的要求,这个消息让我非常兴奋。我们66届的高中生抱着急切的求学愿望,想要通过上大学对人生重新定位。”陶思炎说。
那时他的孩子出生才一个月,复习条件十分艰苦。虽然外语成绩很好,可外语仅作为高考的参考分,而外语系又划定年龄限为25岁,在各种“条件”下,陶思炎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结了缘。“同学中,最大的老三届,最小的十八九岁,年龄参差不齐,但相处很有意思。”
很多读书人会怀念80年代。那些自由的时光,那种一无所有却心系苍生的理想主义情怀,那份一尘不染的爱情,还有那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心。
文学在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复活”。校园广告栏上都是和文学有关的讲座,大小社团亦都是文艺腔。书很多,也很杂,却常常有“轰动效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一出,便争相去图书馆借阅,洛阳纸贵。读小说、读诗歌到半夜是校园常景。校园诗人尤其多,而在自习室里奋笔疾书的并不一定是为了成绩,可能是为了写出“最壮丽”的诗歌献给心上人。
“记得,在一次晚自修教室熄灯后,一位女同学翻窗到教室继续看书,正巧被一位男同学发现了。后来,他就写了一首诗向她致敬,诗就贴在布告栏上。”陶思炎回忆到,“浓厚的文学气息,使我们在大学本科期间夯实了基础。那时,没有奖学金,没有任何的物质奖励,完全是靠精神信仰在学习。”
在中外神话的研究路上偶遇民间文学
“进入中文系后,我首先想选择的是文学史,因为对历史感兴趣。但后来发现在中文系研究历史,自己并没有太多优势。兴趣固然重要,但要和自己的特长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主客观的统一。选择方向就是希望能学有所成,而怎么‘成’就要看自身的长短了。”陶思炎说,“相较而言,外语是我的强项,于是,与文学结合,便开始研究起了外国文学。”
陶思炎的第一外语是俄语,也曾翻译过一些有关普希金研究的文章。为了更好的研究外国文学,他做了很多准备——那时没有复印机,便手抄了两本完整的书,同时,还抄了很多卡片和段落作为资料的原始积累。
“外国文学研究了一年多,有所积累了。但我渐渐发现,即使擅长外语,终究不能和母语国家的文学研究者相比,也就是说,总是借助二手资料难以成为一流大家。于是,我意识到自己要调整,便走上了比较文学之路。”陶思炎说,“比较文学可以在中外文学之间架起桥梁,互相对照,左右逢源。这在当时属于一个新方向,而我则较早地进入了该研究领域,本科毕业时的学士论文写的就是《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
在当时,“神话学”的比较研究是个很新鲜的课题,这篇论文不仅是陶思炎本人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小探,还是他未来学术人生的重要奠基。
“在对神话故事的反复研究中,我发现中外神话其实有很多相通处、共同点。毕业后我一口气写了很多篇关于神话研究的文章,顺带接触到了民间文学。后来,我参加了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民俗学会,1987年报考了北师大的民俗博士。从此就走上了研究民俗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的道路。”陶思炎说。
作为中国第一位民俗文化学博士,陶思炎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至今,出版了专著16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民族译丛》等刊物发表论文近200篇,其中用日文、英文、韩文、越南文在国外发表论文10余篇。现为东南大学教授的他,仍旧精神矍铄的带领着学生在“南京非遗文化”研究的学术路上潜心前行,在挖掘与传承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代南京人:秦淮灯会最有“南京味”
陶思炎对南京的感情很深,用他自己的话说,“算起来,我是第四代南京人,我们家族在南京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在他看来,最有“南京味”的民俗,非秦淮灯会莫属。
秦淮灯会是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民间传统习俗,在每年的春节期间举行,一直延续到观灯最高潮元宵节。秦淮灯会源远流长,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南朝时期,都城南京就出现了举办传统元宵灯会的习俗,其盛况堪称全国之冠。自明初洪武帝朱元璋在南京倡导元宵灯节以后,南京便逐渐开始享有了“灯火(彩)甲天下”的美誉,河悬挂花灯的画舫(俗称“灯船”)随之蜚声天下。
“古时,农历新年期间,全国各地的灯会一般持续六天左右。到了明初,为普天同庆大明太平盛世,朱元璋在南京下令延长放灯日期,起初是十天,之后又有变化,成为全国最长的灯期,这个民俗也一直延续至今。”陶思炎说,“虽然时代变迁,环境在改变,但现在来看,民众热情不减,夫子庙秦淮灯会的灯期能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甚至偶尔会扎灯到阳历三月,这显然已不再局限于‘十八落灯’的这个概念了。”
“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最记忆犹新的还是孩童时对节日的期待感。”陶思炎笑言,历历在目,“那可是最快活的时光了,不仅吃的多,玩的也不少。”
“街头除了皮影戏、独角戏、木偶戏之外,还有杂耍等各种表演,民间艺术家、手艺人的周围往往围满了看新奇的人们。热闹的街上还有许多操持着不同口音,从全国各地来到南京,或是谋生或是赚钱的形形色色路人。”陶思炎说,“那时候南京的艺术气息就很浓厚了,尤其能够感受到南风北俗在此汇集的气息。”
说起夫子庙文化的传世盛誉,陶思炎先生引用了晚晴名儒薛时雨的一副“秦淮河水阁联”——六朝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游,最难忘北国豪情、西园雅集;九曲清波,一帘梦影,楼台依旧好,且消受东山丝竹、南部烟花。
“秦淮风雅,豪气万丈!”陶先生总结。(邬楠 段世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