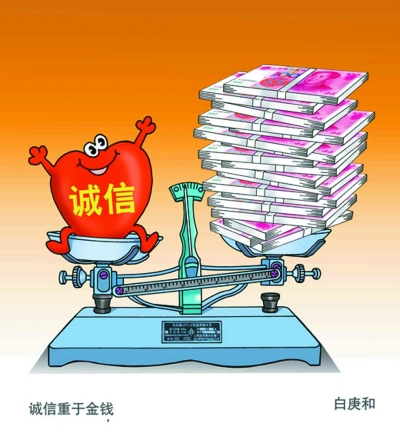2012-09-14 南京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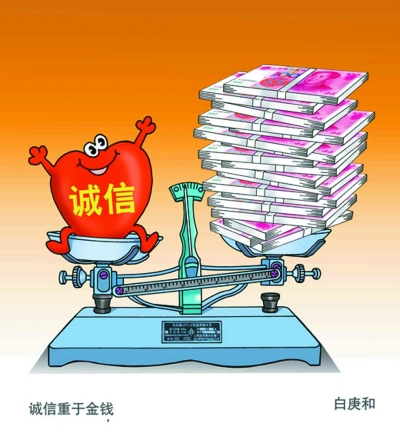
诚信重于金钱

商鞅立木为信

一些人感觉当前社会比过去缺乏诚信,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人际关系将走向何方?其实,只要我们还在为诚信缺失的状况感到担忧,就说明重建诚信社会是有可能的,关键是这条路要怎么走。
【核心观点】
●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人是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中国人是以人与他人的博弈为主,印度人则是以人与自身的博弈为主
●在以人与自然相博弈为主流的社会中,“理”比“情”重;在以人与他人博弈为主流的社会中,“情”比“理”重
●要建立诚信社会,必须要有规则意识,规则要得到所有各方的认同,还要有一个超越所有各方的第三方,目的是保证博弈的公平
吕乃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应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邀请,在东南大学开设人文精品课程《科学与文化的足迹》和《究万物之理》。在中央党校、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和政府部门,中海油等大中小企业做过200余场讲演。
A 对于“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判断,引导东西方文化走上两条大异其趣的道路
社会诚信的走向与这个社会的文化有关,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的判断至关重要。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人的人性观念;而西方人认为人生来有原罪,也就是“性本恶”。我们来看这两种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对于这两种文化的分野产生多大影响:西方,因为性本恶,所以采取底线设计,也就是用“法”来约束人、惩罚恶行,在“法”的底线基础上向上开放,文化特征是发散的;中国,因为性本善,所以采取顶端设计而没有底线,也就是讲伦理道德,树立榜样,向下兼容,文化特征是收敛的,收敛于“圣贤”这一制高点。可以说,“人之初,性本善”的原初假设,是导致诚信缺失现象的根源之一。
那么,人性之初到底是善是恶呢?人之初,可以行善,也可能作恶,从这点上说,性不定。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之初,性已定。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生活于地中海北岸的古代西方人,和生活于长江黄河之滨的古代中国人。地理环境和气候决定了前者的社会生活基础是航海、通商,并且在地中海附近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城邦;而后者以务农为主的自然经济决定了以家庭为主和中央集权的社会组成。特定的时空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人的性格特征,从这点上说,性已定。
在“已定”的“性”中,最重要的是由国学大师梁漱溟所提出的人的三大关系及由此所推及的人的三大博弈。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人是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他们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表现突出,主要是清晰严谨明了的客观知识,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为所有的民族和个人所共享和接受;中国人是以人与他人的博弈为主,产生了一套精妙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像科学那么清楚,有很多难以言说的部分,所谓“你懂的”,个中滋味中国人最明白;印度人则代表了人与自身的博弈,强调信仰、感悟,主张从内心寻找答案,更是神秘莫测,完全依靠个人的悟性。
博弈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锁定”了一个文化的走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来看人与自然的博弈。自然之大,对所有博弈者一视同仁,来者不拒;自然之久,天荒地老,自然界奉陪到底;自然之大、之久的含义还在于,相对于自然界的庞大和久远来说,人类与自然界的博弈及其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自然界“忠贞不渝”,也就是“有限策略”:在同样的语境下,只要与之博弈的人,以相同方式出同一张牌,那么自然界不会变招,也总是出同一张牌,使“重复博弈”成为可能。而人与他人的博弈,则是“无限策略”,所谓“打一枪换个地方”,“无招胜有招”,“兵不厌诈”,“人心叵测”,只能是“一次性博弈”,也只能要求“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与自身博弈,难的是“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历来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由此可见,在三大博弈中,与自然的博弈较为简单。
B 形形色色的“个案处理”或“下不为例”加剧了人际间的失信和背叛
在一个以人与自然相博弈作为主流的社会中,会形成“平权”的视角。客观看待他人和自己,一视同仁;当自然界以同一种状态面对芸芸众生之时,芸芸众生彼此之间也就只能是同一种状态,“平权”,继而由与自然博弈中的“平权”,延伸到人际博弈中的“平权”,各方在“平权”即同一规则下重复博弈。提升诚信的要旨在于延长博弈链,尽可能地重复博弈,这就必须要求各方只能采取“有限策略”,需要有规则并且守规则。人与人之间是“陌生人”,“理”比“情”重。
在一个以人与他人博弈作为主流的社会中,人人都想混成熟人,以进入特定的“圈轮”。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信任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它存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因为信任是私下博弈的产物,信任一个人,是由于他过去的表现守约,值得信任。这个私下博弈的过程依次是双方试探,小规模的信息和情感交换,重复之前的过程直到熟悉对方,演进关系扩展交往,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立信任。在公共博弈中,由所信任者推荐其他可信任的人,形成熟人网络。信任圈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圈,通过亲疏、社会角色等,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圈轮和半径,圈轮向外扩展,信用度就会下降。
本来就如此复杂多变的人际博弈,再加上当代中国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案处理”或“下不为例”,加剧了人际间的失信和背叛。如果没有规则的限定,在情感和利益的驱使下,就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至“情”比“理”重,还有权力的干预等等。于是社会中充斥着无限策略和一次性博弈,在一侧是没有规则,或有规不依,有规不循;另一侧则是权力在规则间肆意妄为。
相比于世界之“刚”,中国体现的是“柔”,即是一种过大的包容,这种柔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导致了司法的所谓“能动性”。我们常说,“原则上”如何如何,这个词在相当程度上开启了不守规则的“后门”。刚性的规则,是社会柔性运行的润滑剂。在没有、或有规则而实际上不完全讲规则的社会里,看似没有刚性规则而可以随意而行,实际上处处是会伤筋动骨的棱角,时时遇到会置于死地的陷阱。从根本上说,正是“个案处理”或“下不为例”,也就是一次性博弈,造成了人际间的失信和背叛。
体育为什么可以沟通不同的文化?按规则来说,体育是一种公平的运动。在体育比赛中,自然界总是默默地参与博弈的一方,即使在涉及人际博弈的球类运动中,对抗双方背后也总是存在一个无言的、对各方一视同仁的参与者——自然。可以说,希腊及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时期,既诞生了作为科学源头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与阿基米德力学,同时也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这并不是巧合。再看看“疑似”体育的中国古代的武功,虽然也有一些规则,但武功修为每每来自机缘或秘籍,因而难以重复,更不能演进。
C 重建社会诚信,要强化规则意识,强化底线,依法治国,对违背规则者零宽容
要建立一个诚信社会,必须要有规则意识。规则要得到所有各方的认同,各方之间能够“平权”,还要有一个超越所有各方的第三方,目的是保证博弈的公平。规则的普遍适用和稳定有效,有助于博弈者在胜负或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积累知识、育成理性、培育信用,从而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
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自然一身而二任,既作为博弈的一方,又是规则的制定者。正是在与自然之间普遍和重复的博弈中,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反复磨练,使得西方人逐步接受和培育了规则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意识推广到人际的博弈中。在一开始就以人际博弈为主的中国,由于博弈各方间充斥着一次性博弈和无限策略,同时,政府作为制定规则的第三方,往往直接参与博弈,如果规则意识淡漠,就会导致守规则的人在一些地方、某些时候反而被淘汰出局,而让善于“变通”者获利,也就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规则得不到执行,而寄希望于伦理道德规范,往往是靠不住的。由于没有对博弈方策略的严格限定,各方随心所欲的“无招”实际上难以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为何在传统文化沿袭的数千年间,中国人不仅讲诚信,而且在世界各国面前堪称礼仪之邦?因为当时的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形成了大大小小由“乡亲们”构建起来的熟人圈,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重复博弈。反过来说,也就是诚信止于熟人。此外,古代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从内心约束和提升人,从外部的远大目标呼唤和引导人,再辅之以淡泊名利之类。简言之,人际博弈的全部弊病在传统社会或者没有“发作”的土壤和环境,或者被规范约束,或者被中国特色的价值理性所引导。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人际之间围绕物质的博弈发生且盛行,但不少人却没有严格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造成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规则”的执行不力,规则的模糊不清,让一些人有空子可钻,在规则外自由“穿越”,这也导致在一次性博弈中,有的遵纪守法者反而输给形形色色的违规者,让博弈走上了逆向的“演进”之路,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由此观之,重建社会诚信不仅需要从每个社会成员做起,还需要强化政府部门的诚信,要有规则意识,然后是强化底线,依法治国,对违背规则者零宽容。
(本报记者吴云青根据吕乃基教授7月14日在南京图书馆的讲座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阅)